美高教社会角色之变

2024年5月28日,学校员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罢工,抗议学校对声援巴勒斯坦的反战抗议活动的处置方式
文/王聪悦
编辑/吴美娜
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围绕联邦资助、学术自由、校园抗议与意识形态站位等问题爆发激烈冲突,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推至了舆论与政治的风暴中心。这场冲突不仅关乎一所高校的命运,更是特朗普政府对所谓“左翼精英堡垒”发起的政治反击,同时揭示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正面临从“知识共同体”向“政治代理体”的角色变迁。
观察人士认为,在政治对立、阶层撕裂与信任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已难以单纯依靠传统学术价值维系其正当性与公信力,而必须直面制度重构与社会角色重估的深刻挑战。
中立性受到空前挑战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由公立与私立高校构成双重核心:公立体系以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为主,承担普及教育与地方人才培养职能;私立体系包括常春藤盟校、研究型大学与文理学院等,靠基金捐赠和市场机制运营,集中于精英教育与科研创新。
自诞生之初,高等教育体系便深深嵌入美国国家建构与社会理想塑造的核心进程中。从美国建国前的9所殖民地学院承担道德训导与精英培养使命,到19世纪赠地大学(land-grant colleges)推动工业化与民主教育并进,再到二战后出台《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角色定位始终以“中立知识共同体”为核心,并从五个方向为美国社会赋能。一是不受政治干扰、追求纯粹学术理性的知识生产中心;二是倡导自由教育、重视思辨、修辞、伦理等基础素养的人才孵化机构;三是提升个体阶层地位、实现“美国梦”、强调机会平等和教育普及的社会流动阶梯;四是承担基础研究、国防科研与技术转化等重要职能的科技创新与国家发展引擎;五是通过人文教育、校园自治、代际传承助力形成稳定文化认同、制度信任的公民意识与民主文化锻造场。
正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相对中立”的角色设定,使其得到社会普遍信任,既能服务国家战略,也能引导社会批判与自我革新。然而,在美国当前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与文化撕裂的大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的中立性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无论是哈佛大学与特朗普政府的“财政对抗”,还是得克萨斯州与佛罗里达州高校课程内容“政治审查”;无论是巴以冲突背景下的校园抗议潮,还是2023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大学以多元化为目标在招生申请中设置种族配额,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已俨然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象牙塔”演化为一个多面向、争议性更强的社会参与体,甚至是政治、社会与文化冲突的“前线阵地”。
新社会角色五大方面
这种新社会角色定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文化战争”的聚焦点。围绕种族平等、性别认同、历史记忆与校园言论自由等议题,左右两派对抗频仍。保守派批评高校灌输“觉醒主义”或“激进自由主义”,自由派则主张将大学打造成包容多元文化与社会正义的实验平台。受此驱动,美国高校不再是文化共识的中介,而日益演变为价值对立的放大器。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布的报告《冲突的代价:文化分裂性冲突对美国公立学校财政的影响》,在近500名受访学区督学中有三分之二表示,他们所在学区因种族、性少数群体(LGBTQ)+学生权利等问题经历了从中度到重度的文化分裂性冲突,干扰教育正常运行之余,还使学校遭到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二是政治代理与社会运动平台。随着“两个美国”不断引爆价值观冲突,加之两党争夺对高等教育系统的主导权,学生与教职员工越来越积极地通过参与环保、反战、移民保护、巴以冲突等公共议题输出立场、表达诉求,迫使校方不断面对是否“选边站队”的压力。高校由此从“中立的知识体”转向“带立场的公共政治体”,校园空间则成为各类社会运动的重要孵化器。
三是阶层再生产机制的被质疑对象。高昂的学费、校友优先录取、标准化考试等问题削弱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平形象。于是,作为高等教育载体的大学既被赋予了“阶层流动的希望”,又被批评为“精英闭环”的象征。
四是公共信任与社会修复的潜在支柱。在传统信任危机蔓延的当下,部分美国高校正尝试通过“事实核查机制”“跨党派对话平台”以及“地方知识再分配”等方式来修复其与公众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重建公共信任与社会正当性。但这种“修复性角色”的重构过程本身并不中立,也无法回避其所承载的政治张力与制度压力。

2024年5月1日凌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跪在警察前
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消除分歧”倡议、哈佛大学的琼·肖伦斯特中心设立的“事实核查”实验室等,旨在对抗虚假信息、提升公共知识质量,但常因涉及疫苗、种族、性别等争议议题而遭到保守派质疑。
五是全球治理与外交领域的复杂角色。在全球化深入推进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不仅参与国际科研合作、吸引海外人才,还通过文化交流和知识生产输出国家软实力。然而,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泛化,这些跨国联系日趋政治化。一些高校的资助或合作关系被联邦政府点名“可能危及国家利益”。美国高校由此逐步演化为地缘政治中的“准外交主体”——既是全球协作体系中的关键力量,又被卷入国家间博弈的前沿阵地,承载着维系开放合作与回应主权焦虑的双重角色,呈现出越来越复杂而敏感的战略地位。
角色嬗变的多重温床
美国高等教育并非主动抛弃中立性,而是在社会信任结构变化、制度碎片化与治理责任转移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了公共争议。换言之,其角色转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高校“自降身份”或选边站队,而是源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结构已发生剧烈变化,使其“中立”地位难以为继。
随着特朗普竞选与执政时期不断攻击“专家”“科学”“学院派”,并将“反高校”情绪制度化为部分选民的动员机制,促使美国社会的左右分裂在教育领域加速凸显。持自由主义倾向的高校常被保守派指责为“左翼意识形态中心”,原本以中立自居的学术空间据此被染上鲜明的政治色彩,在捍卫学术自由与回应社会压力之间陷入两难。
再加上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试图通过经费拨款、签证政策、科研审查等手段影响高校,使高校基金会被迫提高支出比例、调整投资方向,并强化其社会责任,高等教育机构在制度层面难以保持“超然”,逐步卷入党争的战场。
美国中产阶层萎缩与蓝领家庭教育负担加重,更加凸显高校的“双重标签”。
当前,高校仍被视为“向上流动的阶梯”之一。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调查,尽管对高校的“政治中立性”存在争议,但18岁至29岁美国青年群体中,仍有约68%坚信“上大学对成功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以高校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也被指越来越沦为阶层固化的象征。学费飙升、招生偏向,以及精英大学与普通高校之间的资源鸿沟等引发公众对高等教育是否仍在践行“机会平等”的质疑。尤其是在美国低收入群体和农村白人中,高等教育机构被视为脱离现实的“精英堡垒”,成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派”拥趸集中批判的对象。该局面也迫使高等教育机构在回应社会多方不满和正义诉求时,不得不卷入从结构性种族不平等到性别、经济、身份政治等广泛社会议题之中,不仅改变了高校的内部治理,也将其推上了美国“文化战争”的前线。
此外,技术变革的威力也不可小觑。自媒体、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和在线教育等蓬勃兴起,不仅重构着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变相削弱了传统大学的“唯一性”,激起部分公众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是否值得”的质疑声,更重要的是,在社交媒体算法的推波助澜下,“反智主义”声浪被不断放大,互联网的情绪和流量导向矮化了高等教育机构擅长的专业知识“过滤”功能,让“我的感觉”与“专家共识”处于同一传播层级。
加之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判断被贴上“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标签,导致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持续下滑。根据个人权利及表达基金会2024年5月的民调,42%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对美国高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但与2023年美国盖洛普公司的同题调查相比,表示对高校有“极大”或“相当大”信心的美国受访者比例从36%下降到28%,而表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信心的人数则从22%上升为30%。
总体而言,当前美国高等教育正走向多重张力并存、角色重构与路径分化的复杂局面。未来很可能呈现三种趋势并存的状况:一是精英高校继续国际化、平台化,但政府对其政治监管力度加强;二是公立大学系统进一步本地化与“职业化”;三是部分高校尝试扮演社会修复者角色,推动“跨党派对话”“事实核查教育”“地方知识再分配”等社会信任机制重建。
在信任危机、技术激励与身份张力等交织共存的情势下,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将不再是线性进步的延续,而是一个充满斗争、适应与再定义的多轨竞合过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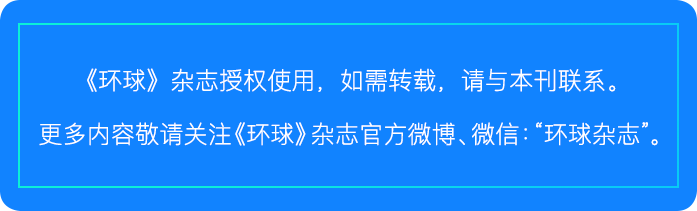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