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与白宫世纪博弈背后

5月2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拍摄的哈佛大学校园
文/张廷芳
编辑/吴美娜
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高校与美国政府方面的冲突仍在发酵。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22日宣布,取消哈佛大学获得的学生和交流学者项目资质,禁止该校招收国际学生。哈佛大学5月23日提起诉讼,批评特朗普政府“公然侵犯”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同日,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对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发出临时限制令,要求在举行听证会之前“维持现状”。
特朗普5月26日再度对哈佛大学发出削减资金威胁,他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正考虑从“非常反犹”的哈佛大学“拿走”30亿美元拨款,并将其分配给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
当哈佛的百年校训“Veritas”(真理)遇上白宫的“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这场较量早已超越法律范畴,它既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种终极测试,更预示着西方知识精英与“民粹政权”全面决裂的开端。
“致命一击”
特朗普2025年1月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后推出“学术问责计划”,该政策要求接受联邦资助的高校必须满足三项标准,即开设“美国传统价值观”必修课程、接受政府指定的科研方向审查、公开所有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来源。
哈佛大学因拒绝执行该计划成为首个被制裁目标,教育部、司法部等五大机构对该校的22.6亿美元拨款与6000万美元合同遭冻结,创下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制裁。哈佛被迫发行7.5亿美元高息债券,这也将该校财政赤字推高至历史峰值。
4月21日,哈佛正式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诉状指控特朗普政府借“学术问责计划”将联邦拨款异化为思想规训工具。
“他们在用财政断流重塑学术DNA。”哈佛大学校长在声明中控诉。
“真正的致命一击”发生在5月22日:冻结拨款、驱逐留学生、课程审查……讽刺的是,美政府指控哈佛“对哈马斯同情”与美国引以为傲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叙事自相矛盾,折射出美国政治话语体系已陷入价值混乱的深渊。
政治极化背景下的“哈佛禁令”
哈佛大学与联邦政府的冲突并非孤立事件。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国防教育法》等政策,逐步将高等教育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联邦资金成为大学科研和运营的重要支柱。特朗普政府此次冻结资金的依据是《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该条款规定联邦资助不得用于“违背国家利益”的研究。这种模糊表述在政治极化背景下成为打压利器。
有数据显示,2020~202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对常春藤盟校的资助削减幅度达37%,其中社会科学和气候变化研究领域降幅超过50%。这种有选择性的资金控制实质上构成了对学术议程的隐形操控: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杠杆决定哪些研究值得资助。哈佛大学的核心诉求,捍卫的正是《美国法典》第20卷中关于“教育机构自治权”的宪法精神。
这种对抗背后是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冲突。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2024年报告显示,全美Top50大学中,注册共和党的教授比例不足12%。学术界的自由派倾向引发保守势力反弹,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资金武器化”重构学术权力格局。这种策略在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地已见端倪,当地立法禁止公立大学教授批判种族理论,如今联邦层面复制了该模式。
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与常春藤联盟存在结构性矛盾。自2016年首次参加总统竞选,特朗普就将精英高校定位为“全球主义堡垒”,其在2024年竞选纲领中更明确承诺:“夺回被左翼意识形态劫持的教育体系。”有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拨款占高校总收入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12%降至2024年的7%,但却不断通过专项资助施加影响力。这种“钱少权大”,反映出保守派试图重构知识生产体系的战略意图。

5月29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警察站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外
5月22日的“哈佛禁令”更是将这种政治干预推向极端。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名禁止招收国际学生,不仅违背美国长期以来的开放传统,更暴露出美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彻底控制学术自由的野心。尽管美国法官的临时叫停为留学生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但这场斗争的最终结局仍悬而未决。若联邦法院最终支持政府主张,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或将遭受致命打击;反之,则可能成为遏制政治权力扩张的关键转折点。
精英大学陷入资本化困局
在联邦审查的阴影下,哈佛大学管理层4月7日作出的市场化融资决策,恰似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这座诞生于清教徒理想的大学,正将校徽烙印在华尔街的债券合约上——最高7.5亿美元的应急融资计划,不仅折射出该校政府资金链断裂的危局,更预示着高等教育资本结构的世纪重构。
532亿美元的捐赠基金(2024年数据)难解燃眉之急。这种从政府拨款、慈善捐赠向金融市场融资的跨越,暴露的不仅是高校财政面临的流动性困境,也显示出其在政治经济双重挤压下的生存策略转型。
显然,学术机构要为资本市场的入场券支付昂贵对价。穆迪2025年给予哈佛债券AA2评级,公然将知识殿堂置于商业显微镜下审视,其背后是信用分析师对大学资产负债表的反复拷问,正在引发人们对学术机构几个世纪以来引以为傲的独立性丧失的担忧。更深刻的异变发生在治理层面:当每年1.5亿美元的债券利息支出成为刚需,图书馆扩建与实验室更新的优先级,或将让位于华尔街期待的资本回报率。这种隐秘的价值重构已出现在公立大学系统。加州大学2024年债券融资占预算23%的现状,昭示美国公共高等教育正在蜕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市场化生存法则催生的资本与精英化纠缠漩涡,正将美国高等教育拖入深渊。哈佛大学2025年突破9万美元的学费门槛与12.3万美元的学生债务中位数,构建起资本循环的封闭回路——越是依赖金融市场输血,越需要维持顶尖学术品牌;而高昂的精英定价策略,又不断侵蚀其社会合法性根基。
这种资本逻辑下的自我强化,在政府公共资金战略性撤退的背景下形成致命加速度: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领域外的学科收缩、社区学院系统的倒闭潮(2024年关闭了47所),以及皮尤研究中心揭示的68%共和党支持者对精英大学教授们的敌视,共同勾勒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政治资本夹缝中扭曲生长的生存图景。
美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契约危机
美国高等教育社会契约的逐渐消解,是这场风暴诞生的真正根源所在。二战后确立的“政府资助-学术自由-公共服务”三角平衡,在政治极化与技术革命的夹击下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民调揭示,58%的美国人认为大学“对国家发展有害”,共和党支持者中持此观点的比例更高达79%。
三个结构性矛盾始终在塑造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的地貌,即知识生产与公共利益的脱节、精英再生产与社会流动的断裂、全球化与本土认同的撕裂。而在本次美政府针对个别名校的全方位打压下,本已错综的矛盾更趋复杂和难解。
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尖端领域的研究,正从公共知识库蜕变为资本竞技场。哈佛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2024年专利收入3.2亿美元,远远高于其社区服务支出金额。这种异化在政府资助体系上形成吊诡循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显示,联邦资金覆盖了顶尖大学73%基础研究项目,但资金冻结威胁下,2027年可能出现人工智能博士培养量骤降28%、材料科学专利减少19%、量子计算研究延迟4~5年的技术危机,与所谓“美国优先”严重相悖。
精英再生产机制正在消解高等教育的社会合法性。哈佛2025届新生中,家庭收入前1%群体占比达28%,捐赠生录取率是普通申请者的7倍,数据背后隐现的阶层固化正在加速。一旦联邦资助成为维系研究体系的命脉,政治力量便获得了重塑学术版图的杠杆。特朗普政府冻结人文社科资金的举措,实质是对“非实用学科”的系统清洗。这种工具理性至上的治理模式,暴露出资本逻辑与人文精神的根本冲突。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撕裂则在校园投下更深的阴影。有数据显示,国际学生在哈佛研究生院占43%,贡献了科技领域60%的研发力量,但“学术本土化”政策强制STEM专业本土生比例不得低于75%,这种逆全球化浪潮正在侵蚀研究型大学的根基。更深刻的危机在于,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政治博弈的镜像战场——68%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大学教授传播有害思想”,十年时间41个百分点的增幅背后,是“美国文化复兴运动”对学术场域的全方位渗透。
事态发展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治理范式的转换。美政府以资助为杠杆、以认证为武器、以数据监控为条件重构高校治理规则,改写着学术自由的边界,更动摇了知识生产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契约。而技术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双重夹击,让美国高校面临自麦卡锡时代以来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名校们”的突围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正被迫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和撕裂中寻找出路。
例如,加州大学系统启动的“知识公地计划”开创公共化改革先河,通过将25%的核心研究成果转为开放获取,构建起“知识共享-财政支持”的新型契约关系,其今年获得的12亿美元特别拨款印证了知识公共品属性的价值回归。而麻省理工学院与“元”公司(Meta)共建的元宇宙校区则彰显技术化生存路径,其虚拟现实教学系统不仅将运营成本压缩至传统模式的45%,更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学术成果的确权与流通,这种数字生产关系重构使在线硕士项目的学费定价权首次脱离实体校园的成本框架。更具突破性的是芝加哥大学实施的“邻里实验室”计划,该方案将49%的科研预算定向投入社区问题研究,通过建立居民参与式研究委员会,使癌症筛查技术开发周期缩短40%,这种在地化创新模式正在重塑大学的社会信任资本。
但这一转型进程正遭遇制度性阻碍。比如,美联邦政府援引《高等教育法》第123条扩大了监管权。虽然该条款自1972年颁布以来仅适用于财务审计,美国教育部近期却据此要求审查STEM专业课程中的“意识形态偏差”。宪法学者警告,若最高法院认可行政机构对学术内容的干预权,将突破“立法授权”原则的宪法边界,导致联邦机构自由裁量权的系统性扩张。
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求哈佛提交留学生“非法活动”档案,让很多人想起麦卡锡时代的黑色档案柜;政府以“校园安全”为由切断国际生源,与1950年代“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审查教授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当前的权力博弈增添了技术寡头的新变量。联邦拨款、科技巨头捐赠与学费收入构成的“黄金三角”,使大学在抵抗政治干预时始终难以挣脱利益的枷锁。
美联邦机构挥舞行政大棒,州议会酝酿《学术自由盾牌法案》,科技资本通过研究资助设置隐形议程,而教授委员会则试图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百年章程捍卫最后防线……在知识权力重构的漩涡中,多元主体博弈的复杂图景正在呈现。这种撕裂将导致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出现“红蓝分校”现象——保守州州立大学加速意识形态转向,而精英私校则可能退守为全球化知识飞地。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所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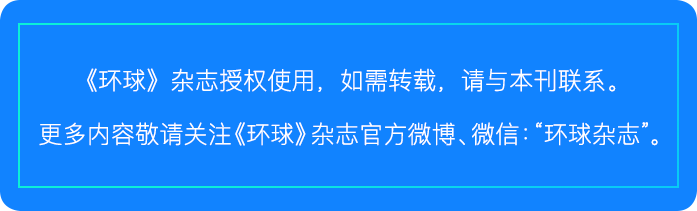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